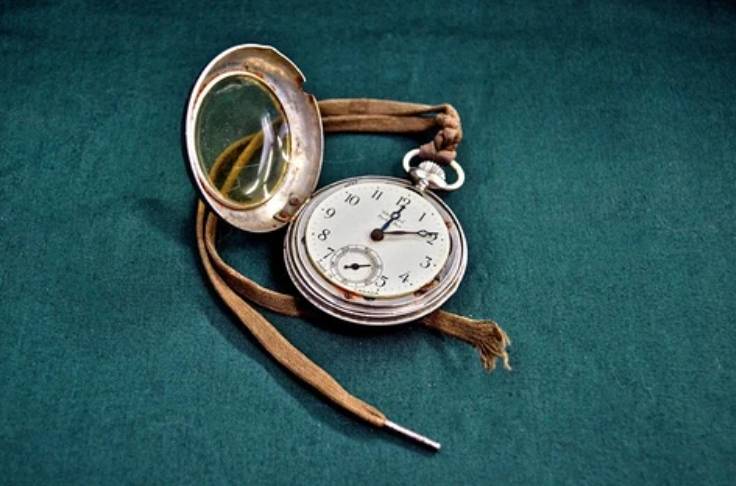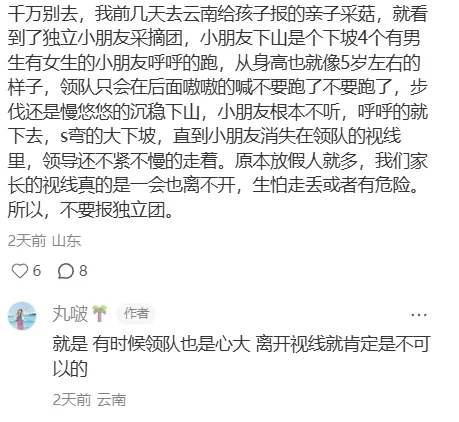一
八月本是大理研学营收割家长钱包的季节,却因一名 8 岁自闭症男童在苍山走失,瞬间变成全民焦点。
最新消息显示,昨日,当地救援力量已经增至 600 余人次,开始拉网式搜索。可大雨、低温让搜救难度陡增。
民宿、商户自发捐赠物资,民间志愿者也在持续支援,人们还在苦苦等待好消息,只盼孩子平安。
与此同时,在舆论场的另一头,是大理研学市场的急速刹车。
事情发生后,我给在大理做 「独立营」 研学多年的朋友 A 小姐打了个电话。
她的声音很平淡,和我说,今年暑期已经算是收尾了,「手上这一批孩子带完,后面退的退,剩下半个月就佛系躺平了,这个时候谁还敢节外生枝?」
在社交媒体上,更多已经报了大理独立营研学的妈妈们,心态彻底崩了。
有人写道:「打开小红书,大理天塌了,报了下周的独立营,现在有点慌。去还是不去?真心希望孩子快快找到靠谱的去处,希望各种营也能仔细培训老师,加强防范措施。」
评论区迅速变成大型劝退现场。
一位家长复盘了自己在大理的见闻:前几天给孩子报了亲子采菇,路上看见小朋友独立采摘团,下山是个大下坡,四个五岁左右的小朋友 「呼呼地跑」,领队只在后面喊 「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人多,弯急,孩子直到消失在视线里,领队仍在不紧不慢地走。」
她的结论很决绝:所以不要报独立营。
另一条反馈更是直指大理研学的不透明氛围。
一位给孩子报名了大理研学的家长回忆自己的报名经过,她说,大理的所有 「营」,信息又乱又杂。
「我当时给娃找,只能通过小红书或者加老师微信,纯粹是靠小红书口碑去筛选,哪家大家都说好,哪家大家都说不好,只能自己判断,现在想想,也是后怕。」
这些直白的劝退,在以前几乎是看不到的。
而家长的恐惧,往往源于独立营的信息不对称与过程不可见——谁在带?怎么带?应急怎么做?
在大理,原本该被清晰写进 SOP 的环节,却常常被小红书文案、朋友圈海报所替代,原本该在日常训练中打磨的组织与响应,在现实里却被临时拼凑与拍照打卡所稀释。
这些细节原本无人注意,直到 8 岁男童在苍山走失后,这才让很多父母意识到,原来心目中浪漫、安全、适合孩子亲近自然的大理独立营研学竟然藏着如此多的风险。
二
2022 年,我带孩子在大理旅居了一年。
客观来说,那段时间,我发现,大理研学并不是现在外界想象中的那样,「全是网红和糊弄事」,靠谱的机构和幼儿园确实有,还做得很好。
比如我孩子上的幼儿园,老师认真负责,没事就带这些小朋友去洱海边认识植物,节假日去喜洲插秧、做农活,孩子回来一身泥,脸上全是笑。
这些活动简单、真实、接地气,没有商业包装的虚火,却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自然。
大理某农场研学/旅界实拍
但同时,大理的研学市场也确实是鱼龙混杂。
你能在同一条街上看到用心打磨课程的团队,也能遇到贴个营地牌子就招生的皮包公司。
第一次让我惊讶大理 「万物皆可研学」 的是一次用餐经历,我常去吃饭的一家小餐馆,突然在门口挂出一块木牌——「少儿厨艺研学营招生」。
那家餐厅平时只做几道家常菜,连厨房都是半开放的,老板娘笑嘻嘻地对我说:「反正暑假人多,正好教小孩做喜洲粑粑,还能顺便收点学费。」
我看着她忙着切菜、炒锅,脑子里浮现的是十几个孩子围着这口油烟扑面的灶台转圈的画面,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长时间教学的地方,但在大理,这些草台班子并不少见。
还有一次,我在海东的一个小村子访友,遇见一位民宿老板,他一边给我泡茶,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我们下个月打算搞禅修研学,带孩子在院子里打坐,听海风,看日出,感悟人生。」
大理海东眺望苍山/旅界实拍
我忍不住问:「孩子多大啊?」
他想了想:「小学生就行吧,小红书打了几轮广告,家长很愿意送来。」
我当时没接话,只能在心里叹口气,在这里,研学的边界早就被无限拉伸,从动手做饭到静坐冥想,什么都能被包装成课程卖出去。
这种,高利润、低门槛,无数人蜂拥而入。
很多新玩家的心思不在课程,而在于 「怎么抓住这波暑期客流」,于是,营销比内容更重要,拍照比教学更用心,真正踏实做经营的机构,反而在一轮轮价格战和口碑稀释中,被挤到角落。
我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在大理做了六年自然教育,每次户外活动都要求老师提前踩点、做应急演练,要求把所有细节写进方案,哪怕临时换路线也能照着执行。
可这几年,他越来越难招到学生,家长被短视频里的 「低价高体验」 吸走了,本地同行却劝他 「别那么认真,赚不着钱」。
他苦笑着对我说:「认真做研学的,最后不是亏钱走人,就是被迫学着别人那套凑合办法。」
这就是大理研学的悖论,风景是真的好,孩子也能在这里亲近自然,但在光鲜照片背后,混乱的生态正在一点点吞噬那些原本想把事做好的人。
三
对 8 岁男童的搜救行动还在继续,这次大理想你的风没有吹在苍山洱海上,却吹进了每一个家长的心里。
据媒体公开报道,此次涉事的 「明日之光」 研学营在当地开了一两年,租的是村民的房子,孩子全是从外地来的,平时这里大门紧锁,偶尔老师带队外出,才能在路上看到他们的影子。
站在隔壁房子的高处望进去,院子里摆着孩子的床铺、书桌、生活用品,它更像是一栋封闭的宿舍楼,而非海报里阳光、自由、亲近自然的独立营。
更吊诡的是,在大理,这类机构究竟归谁管,没人能立刻说清。
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承认,在教育系统中注册的多是跳舞、唱歌、书法之类的培训,有些归民政,有些干脆没登记。
研学,就这样在教育与文旅的夹缝里,长成了一个谁都能插一脚的市场。
市场疯长,监管滞后,所以这一次,大理研学市场洗牌是必然的。
入口要设门槛,谁能办研学、需要什么资质,必须有一个统一标准。
过程中要设监督哨兵,课程、师资、师生比例、安全预案、线路评估,除了写在简章里给家长看,也要有人定期去现场查。
监管也不能只在出事后才出现。
可以想见,洗牌会让大理研学市场萧条一阵子,但对大理来说,研学机构少了并非坏事,那些被埋没在噪音里的好机构重见天日反而是幸事。
其实放大到全国,暑期研学的问题和大理并无二致。
之前旅界曾发文 《暑期研学也割不动家长了?》,这届家长早就不是 「掏钱买概念」 的那一批人了,他们愿意花钱,但前提是孩子能在研学里真正学到东西,带着收获回家。
风景、课程、故事,这些都是加分项,安全、价值、专业,才是决定家长是否买单的底线。
家长不怕贵,不怕远,怕的是花了钱,换来的只是一张好看的照片和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
而大理研学,如果想留住这群最挑剔、也最愿意付费的家长,必须先让他们放心。
毕竟风可以吹遍苍山洱海,但信任只会留给值得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旅界 (ID:tourismzonenews),作者:theodore 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