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刀客 Doc
一、至暗时刻?
6 月 11 日,快消巨头玛氏公司宣布其价值 17 亿美元,在全球 70 个市场的广告业务交给阳狮集团,这其中包括 M&M's、士力架、宝路等知名品牌。
此前,玛氏公司一直是 WPP 的大客户。早在今年 3 月,WPP 就丢掉了可口可乐在北美的媒体业务,随后电影公司派拉蒙也结束了与 WPP 长达 20 年的合作关系。
对 WPP 来说,这不是最坏的消息。2024 年底的时候,WPP 营收排名第一的宝座被法国竞争对手阳狮集团夺走。
6 月 8 日,WPP 首席执行官马克·里德 (Mark Read) 宣布将卸任,里德在 WPP 集团任职长达 30 年,担任 CEO 也有七年时间。
里德的离职半年前就已经有传闻。今年年初,前英国电信 (BT) 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詹森 (Philip Jansen) 出任 WPP 董事长,当时就已经引发了行业对里德离职的猜测。据英国 《卫报》 的报道,「詹森在正式上任董事长几个月前,就开始向公司高管征求意见。同时他也积极从基层征求建议,了解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 一位 WPP 高管说道。「他的很多调查角度都与里德的改革有关。」
很多人认为:里德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他需要为当下 WPP 的业绩表现负责。
里德离职的消息发布后,WPP 集团的股价在周一当天下跌了 1.5%。截至发稿前,WPP 市值是 80.76 亿美元,而 2018 年 WPP 有 235 亿美元的市值,跌幅是 65.6%。

根据今年 Q1 财报,WPP 集团营收下降 5%,股价同比下跌 29%。从地区来看,虽然北美市场以 0.1% 的微弱降幅企稳基本盘,但其他核心市场集体失速——英国市场受本土零售业衰退及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收入缩水 5.5%;西欧受德国经济疲软主导,整体下降 4.5%;新兴市场板块虽整体下滑 3.8%,尤其是中国市场遭遇 17.4% 大幅下跌。
与之相比,同期的阳狮集团净收入增长 9.4%,有机增长 4.9%。如果自己的竞争对手还在保持增长,那么 WPP 就不能简单地甩锅给大环境。
另外,科技巨头的触角一步步伸到广告行业的核心领地。就在月初,Meta 宣布 2026 年推出完全自动化的 AI 广告,广告主只需提供想要推广的产品图片以及预算目标,AI 就能生成整个广告,包括图片、视频和文字。
这在广告业引发了不小的恐慌。尽管扎克伯格声称:」 这只是对中小企业的赋能举措,广告人的创意才华依然不会被取代。」 但是这些年面对科技巨头一步步的渗透,广告业早已对这种烟雾弹免疫了。
领导人出走、王座易主、大单频失、业绩和股价持续下滑,再加上科技巨头携 AI 技术的侵袭。不管从哪个层面来看,WPP 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终归迎来了自己的至暗时刻。
英国的营销媒体尖锐指出:一向习惯了狩猎他人的 WPP,未来会不会成为别人收购的猎物?
二、散装的结构
2018 年,WPP 创始人苏铭天 (Martin Sorrell) 离职,马克·里德 (Mark Read) 接任 CEO,中文名叫睿智德,不过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在国内流传开来,我们还是称呼他 「里德」。
里德接手的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组织,用 WPP 的一位股东的话说就是 「杂乱无章」。
苏铭天时代,WPP 秉持着激进的并购扩张策略,每年平均收购超 10 家公司。以至于到 2018 年里德上任 CEO 的时候,WPP 旗下独立运营的代理机构已经超过 400 个,涵盖广告创意、媒介投放、公关咨询、市场研究等多个营销领域。400 个机构里,群邑、凯度等主力代理厂牌约 60 家,其余多为区域型工作室或细分领域机构。
国内的营销行业媒体 《广告狂人》 曾经做过一个 2016 年 WPP 集团的图谱,各位可以感受下。

这给行业投射了一个很有趣的形象:WPP 旗下的奥美集团被认为是一个创意驱动的代理公司,而 WPP 自己留给市场的形象却是一个金融驱动的机构。一位现任高管对美国财经媒体 《商业内幕》 说:「WPP 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旨在收购代理机构并回报股东的投资工具。」
很明显的是,400 多个机构没有实现有效整合,大家各自为政,形成了一个的 「散装集团」。
当然,这种看上去散装的组织网络是适配于当时的营销环境的。我分析两个原因:
1、按照一个代理商服务行业一个公司的原则,这样会减少不必要的客户冲突和竞争,能拿到更多品牌的业务。
2、在以前的营销环境下,创意、媒介投放、公关等专业领域相对独立,营销渠道也比较有限,客户的需求和目标相对明确且各自分离。因此,多机构之间不需要更多的协同,大家各自把创意和媒介执行做好就行。
不过这几年数字营销环境发生剧变,AI 技术和数据驱动的数字营销逐渐成为主流,Meta、Google 等巨头通过广告技术生态掌控用户行为数据,导致广告主高度依赖平台的数据资源,而 WPP 等传统代理集团因内部技术分散和数据整合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平台化、实时化需求。具体表现为:
品牌割裂:子公司保留独立运营权,导致资源重复配置。比如扬罗必凯与 VML 两家公司并存数字业务,内部竞争削弱协同效率。7 年前,第三方咨询机构 Forrester 认识到 WPP 的复杂性,建议他将旗下众多代理机构整合成少数几个核心网络,并让其媒体代理机构 「以单一的群邑集团 (GroupM) 运营」。事实证明,这个建议非常具有预见性了。
响应迟滞:效率低下是资深广告专业人士最担心的问题。根据行业调查机构 Basis Technologies 的研究,56.1% 的广告公司领导认为流程效率低下是代理商面临的最大挑战。Basis 报告中提到的许多问题 (运营拖延、系统脱节和成本膨胀) 反映了 WPP 在里德领导下面临的挑战。当时,全球最大广告主宝洁,其 CMO 就曾经在美国广告主大会上吐槽:
「许多广告集团过多的管理、高昂的租金和间接费用让广告主显得力不从心。代理公司的业务更加复杂,层层客户经理来传达信息,导致广告公司不再关注创意,过多的时间花在电话会议、场外活动、差旅、PPT 汇报上。」
技术脱节:数字业务分散于伟门、AKQA 等代理品牌,各代理机构长期独立运营形成的技术壁垒尚未完全打通,导致在对抗 Meta、Google 的算法优势时明显吃力。
三、彻底进化
针对以上问题,上任后的里德随即提出了著名的 Radical Evolution 方略,中文译为 「彻底进化」 或 「激进进化」,主要围绕愿景、创新、技术、架构和文化等 5 个方面推进。
这 5 个举措,我用一个国内互联网行业的时髦词汇形容就是 「去肥增瘦」。也就是内部裁撤冗余机构,组织效率整合,实现大一统的集权,提升效率和敏捷度。外部持续并购加强技术赋能,顺应目前技术主导下的营销环境。2021 年里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三年间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对 WPP 架构和企业文化的改变。
1、去肥:内部机构的裁撤与合并
在内部整合的动作上,我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2018 年 9 月,数字代理商 VML 与百年创意老店扬罗必凯 (Y&R) 合并为 VML Y&R。
同年 11 月,智威汤逊 (JWT) 与伟门 (Wunderman) 合并为伟门智威(Wunderman Thompson)。
2019 年通过 36 次非核心业务出售 (如市场研究公司凯度部分股权),筹集 8.49 亿英镑现金,缓解财务压力。
2020 年 11 月,百年广告公司葛瑞 (Grey) 与数字先锋 AKQA 合并为 AKQA 集团,强化用户体验设计能力。
2023 年 10 月,将伟门智威与 VMLY&R 二次合并为 VML,诞生全球最大创意公司 (3 万名员工),整合品牌体验、客户数据与商业转化能力。
2024 年 1 月,公关巨头伟达 (Hill & Knowlton) 与博雅 (BCW) 合并为 Burson 集团(年收入 12.7 亿美元),专注声誉管理与危机公关。
2025 年将旗下媒介代理品牌群邑 (GroupM) 重组为统一实体 「WPP Media」,关停冗余架构,裁员比例达 40%-45%。此举将传立、蔚迈等媒介子公司纳入统一管理,减少内耗并简化客户对接流程。
「苏铭天爵士打造了帝国」,而里德重构了帝国」。独立媒体分析师亚历克斯·德格鲁特 (Alex DeGroote) 计算,里德任期内淘汰了约 300 个不同的代理品牌,关闭了 800 多个办事处。
一系列的合并动作确实实现了简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过去几年,WPP 旗下各代理机构的领导层经常会以相互矛盾的观点对待客户,新的架构大大减少了这种内讧。
里德对内部成本的控制变得宽松了一些,位前 WPP 媒体代理公司高管表示,里德似乎更信任代理公司领导层自行管理预算,而且不像他的前任苏铭天那样强调紧缩开支。
另外里德还在继续推行 WPP 的 Campus 项目,这一项目主要是改变传统分散的办公模式,将旗下奥美、群邑、伟门智威等原分散运营的子品牌团队集中迁移至统一空间。
例如 2023 年启用的广州办公园区,汇集奥美、群邑、伟门智威等 7 家公司、500 多名员工,通过 「Campus」 设计促进跨团队协作,强化彼此交流。
2、增瘦:合作 AI,收购技术公司
里德将 AI 定位为 「行业最大机遇」,他希望在未来几年通过构建数据、电子商务和营销技术服务来脱颖而出,而不是像过去 35 年那样收购更多的代理商。他在任内的并购聚焦两类技术企业:
1、AI 内容生成领域:2024 年投资英国多模态初创公司 Stability AI,利用其图像与视频生成技术优化营销内容生产;同时参股 AI 内容工具商,与英伟达共建 「Production Studio」 实现文本、图像、视频的自动化生成。
2、社交与数据技术领域:2021 年战略投资中国营销技术公司 StarEngine,联合开发社交内容营销产品,帮助品牌管理 KOL 投放并提升电商转化率。尤其是 2025 年,里德进一步收购数据协作平台 InfoSum,强化隐私安全的数据处理能力。
里德每年投入超 3 亿英镑构建自研智能营销操作系统 WPP Open。该系统整合了创意生产、媒介投放与数据分析全链路能力,并嵌入生成式 AI 工具。
至 2025 年 3 月,WPP Open 已覆盖 4.8 万名员工 (占客户服务团队的 60%),为吉百利印度市场生成 13 万条个性化广告,触达 9400 万人,成本降低 90%。里德通过 「未来就绪学院」(Future Readiness Academy) 培训 5 万名员工使用 AI 工具。
看上去,正在一切都在走向正轨。
四、未竟的变革
从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看,WPP 当时的战略方向真的没什么问题,不过战略的 「正确性」 未能抵消执行过程中的震荡与撕裂。
里德时代的持续重组和裁员不断打击了普通员工的士气。2018 年,WPP 全球员工总数约为 13.4 万人,2024 年的时候降至 10.8 万人。
员工的反对声音日益明显,也愈发尖锐,也终于在今年年初爆发。
1 月份,WPP 取消了远程居家办公,强制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四天在办公室。里德认为,办公室出勤率和财务业绩密切相关。
这引发了员工的强烈发对,他们发起请愿,要求 WPP 重新考虑其政策。这份请愿书得到了 1.5 万多 WPP 员工的签名。
当然强制员工四天回职场办公并不是什么苛刻政策,谷歌、亚马逊、苹果、Meta 都坚持要求员工全职返岗。甚至连竞争对手阳狮集团还裁掉了不愿意返岗的员工,就这也没有引发这么大的反应。
而 1.5 万 WPP 员工却集体情愿,这本身反映了内部沟通的问题以及员工的焦虑情绪,最终导致内部的士气比较低落。
不只是内部士气不足,里德引以为傲的组织重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很多决策让人匪夷所思,最典型的就是裁撤厂牌。
自 2018 年以来,包括博雅公关 (1953 年成立)、扬·罗比凯 (1923 年成立) 和葛瑞 Grey(1917 年成立) 等广告厂牌都被停用。
据媒体 《商业内幕》 报道:「合并后的第一年,Grey 和 AKQA 仍然是两家截然不同的公司,除了新的业务方案之外,从未有过像样的合作。」
里德对此并着急,他认为只要能招到最好的人才,品牌 CMO 们并不关心与哪家代理公司合作。「WPP 拥有 9 个创意网络,而 Omnicom 和 IPG 等竞争对手只有 3 到 4 个,需要简化这些网络能更好地服务客户。」
不过客户似乎并不买账。据 《广告时代》 报道,宝洁公司 CMO 马克·普里查德曾经要求 WPP 保留 Grey 的厂牌名称。
里德停用的厂牌有的时几十年历史,甚至有的是百年老字号,而他似乎为了体现与传统决裂,一夜之间放弃了数十年的品牌价值。这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 2018 年 11 月伟门 (Wunderman) 与 JWT(J.Walter Thompson) 的合并,随后 JWT 厂牌成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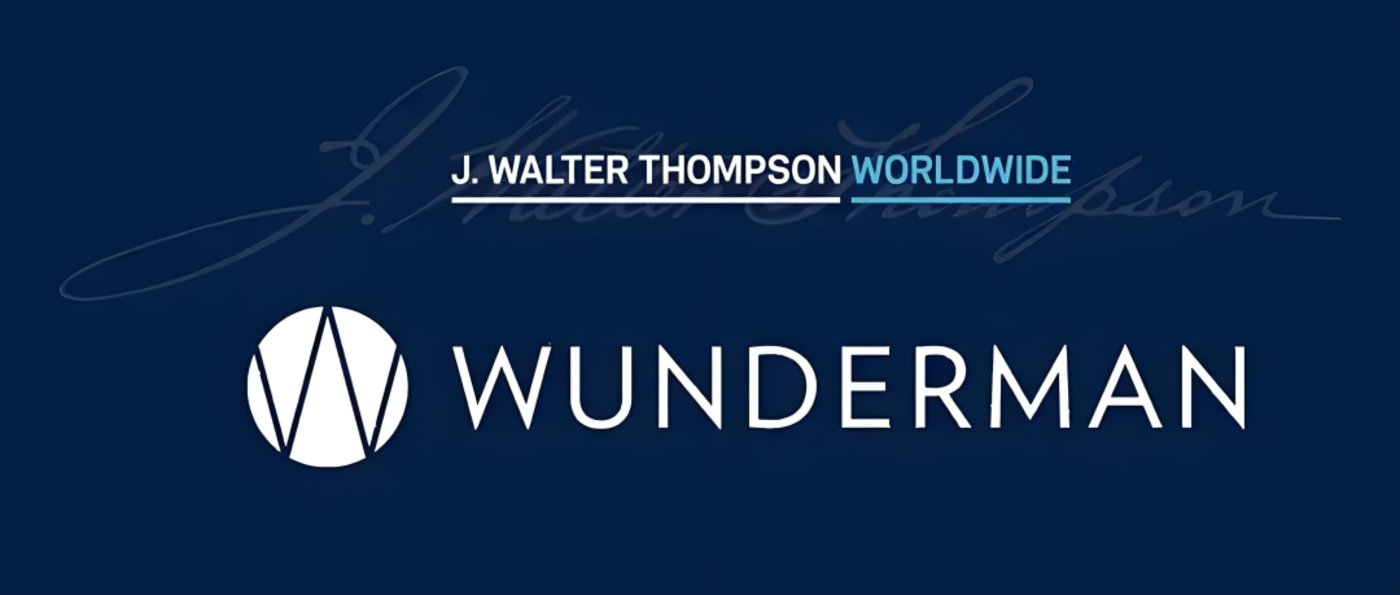
「我们抹掉了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有业内人士遗憾地说。
JWT 成立于 1864 年,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广告公司。一位 WPP 员工表示:JWT 在印度、亚太等关键市场获得广泛认可,但那里的客户从未听说过 Wunderman,也不了解此次合并对他们的业务意味着什么。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在执掌 WPP 之前,里德曾担任伟门的全球首席执行官,所以他更青睐伟门,而非 JWT。
「用 VML 取代知名创意公司 JW 和扬·罗必凯的品牌,究竟有何道理?VML 是一家知名度较低、成立时间较短的广告公司,最初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堪萨斯州。在堪萨斯城以外,VML 啥都不是!」 一位前 WPP 高管说。
另外,尽管里德一直在做投资新科技新技术,但华尔街一直都不认为 WPP 是一家科技公司。
「现实情况是,市场只是愿意对 IT 咨询领域的公司和一些平台业务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 花旗银行的分析师托马斯·辛格赫斯特曾预测,WPP 在可预见的未来年收入有机增长率仅为个位数,广告代理业务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远高于这一水平。
「企业的 AI 化,不是投资一系列 AI 公司,买入更多的数据。而是要让生产工具转化成生产力,所以效率是当下最重要的指标。单靠 AI 人工智能无法解决臃肿的系统——代理公司需要的是工作流程的简化、数据的凝聚力以及鼓励灵活性的商业模式。」
五、老大走了
现在,里德也要离开了,而且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巨头和广告集团交锋的关键时刻。
行业分析师称:「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的离开,在这个时候,做出人事变动的决定,这表明公司内部高层之间没有达成统一共识。新任 CEO 可能还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到那时 WPP 那些更精通技术的竞争对手可能会领先更多。」
在外界看来,里德和苏铭天确实是截然不同的管理者。
「有人可以管理整个集团吗?没人能像他 (苏铭天) 做得那样。」 很早之前,里德曾经这样评价 WPP 创始人苏铭天。苏铭天最明显的特征是激进,是典型的 「强人风格」。
而在很多媒体看来,里德过于内敛低调。这种温和协同的特质,体现在他培育 「包容、尊重、合作」 文化的公开宣言中,也渗透于 WPP Open 平台试图打通内部协作的底层设计。
总之,对 WPP 这种广告大厂而言,转型实在太难了。尤其是在与科技巨头的对决时刻,更需要大刀阔斧的举措,需要义无反顾的雄心。温和派改良不能阻挡阳狮集团的超越,不能抵挡科技巨头的侵袭,最终也不能做到力挽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