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 8 月 12 日,是我作为美国社区大学全职学生上课的第一天。
收拾书包时,一年前的画面清晰浮现。那时,我计划从 2024 年 7 月中旬开始,在北卡 UNC 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后申请延期——J1 签证最长可达 5 年。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条原本看似顺理成章的路,因为各种外部因素突然转弯。今夏,我没有继续做访问学者,而是转成学签,走进了大学,成为一个有些茫然的大龄学生。
说实话,当年离开家乡,坐一夜绿皮火车去兰州上大学时,我也没这么紧张,毕竟,毕业后这 26 年的散漫自由、追求 「无用」 之学、人到中年性格乖张,很难重新走进青年时听话乖巧、老实听课、应付考试的 「泡泡」 之中。
题图:路边的无花果一天天成熟了,果实低垂,正待膨胀。
今天听丹青老师的 《文学回忆录》 第二季 《离题而谈》 开篇,他说了一句话:「我喜欢这种状态。什么状态呢?走到哪里是哪里,完全不知道下一集讲些什么,甚至下一句讲些什么,我喜欢这种状态。」
这句话治愈了那一分那一秒的我——这是一种人到中 (老)年的年轻心态啊!
我正慢跑,穿过一片空旷的树林。一条不宽的沥青路向左蜿蜒而去,路中间平整,两边微微塌陷,形成自然的弧形,又像是两侧树木的光影造成的错觉。脚步声、呼吸声,与不知何处传来的鸟鸣交织,提醒我,眼下这一刻才是真实的。

我在过去的文章里提到过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一书,如果抛开 「伟大」 不谈,正常的生活本身也是不能被百分百计划的。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 「走一步,看一步」。
年纪越大越明白,这句话的内涵并不是逃避,而是当你无数次面对不确定时,选择 「不逃」 的心理历程。
如果有机会对 20 年前的我说一句话,我会说:没关系;今天,我对自己说 「嗐,走到哪里算哪里吧!」 我认为,它不是摆烂,而是一种难得的笃定,只管先好好走出一步,让这一步的全力以赴,成为下一步的基石。
我觉得,它本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但方式也只是方式,活在其间的人是不是意识到了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意识地具备这种心态,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正念所指吧。
我并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真相,事实上,过去多年的亲身经历,都在慢慢向我暗示这一点。
不管是曾经每周必须完成两个报纸版面的稿件组织,还是一次次全程马拉松比赛的策略,或者来美国一年里从 「躺平式」 访学到全职学生的转变……大到人生不同阶段,到每一天的安排、每一份职业的对待,小到一件任务的处理,都面临抉择。
生出的焦虑和压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大多是情绪垃圾,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
真正有帮助的,是告诉自己:「走到哪里是哪里」,隐藏在这句话里没有明说的是另一句:你应该、也可以走好此刻脚下这一步。
蒙田在 《随笔集》 里说:「我不走最远的路,也不追最短的路,我只走我此刻能走的路。」 这是多么有勇气的对自我的诚实!
昨晚,在预习课程时,我发现大纲里的内容多到一个网页装不下,对学科合格的门槛也很高——整学期成绩要达到 80 分以上,不仅日常作业量大,还要求课外每周至少 10 小时的练习。
虽然我的英语水平测试是 Level 4,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真正进入学术水平的阅读与写作,对离开校园 26 年、快 50 岁的我来说,仍是巨大的挑战。
「走到哪里是哪里」 这句话,正好给了我力量,让我从一瞬间的慌乱中冷静下来:好好预习准备,笨拙而认真地对待每一堂课,不问难度和强度,耐心 「打怪」,不问结果和分数,专注过程。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老师的尊重。
这种力量就像其中一篇关于 Metacognition(元认知)的文章所说:
Once you start recognizing patterns, hiccups, problems, solutions, and good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you』ll be more involved in your learning – and you』ll be better prepared to tackle more challenging assignments. Remember: learning takes time. Everyone has to struggle through difficult tasks.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is that we can look back and see how we were able to conquer those challenges – what tools we used and what strategies we employed.
这种 「走到哪里是哪里」 的心态,并不是消极的听天由命,更多地,是一种主动的松弛。
它像是水。水不会预设流向,但它总能抵达大海。
过去,活在确定性强的时代的我们常喜欢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行动前一定先要规划,才能保证安全。但如今,「预」 带不来真正的安全感,对不确定性的接纳和应对,会不会更有帮助一点?
其实,在很长一段历史里,人类都不是生活在确定中,而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
农业社会看天吃饭,渔民靠潮汐谋生,行商依季节和路况决定下一站,他们并不是不想计划,而是知道计划本身是脆弱的。
「人定胜天」 这个词,被中国人简化并误解太久了。在董仲舒的语境中,这个词不是说人类可以完全战胜自然,而是强调在人事、政治、社会秩序上,通过人力与智慧是可以改变天命趋势的。
古人的 「不确定」,一方面来自物质条件有限和生活节奏缓慢,同时也来自外部环境的巨大波动——一场战事、一轮饥荒、一次政权更替,都可能彻底改变个人和宗族命运。我们在史书中看过不少此类故事。
而现代人的 「不确定」,并不是环境变得稳定了,只是它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全球化已转向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摩擦、贸易战频繁、供应链重组,使得经济和行业的周期被压缩,外部冲击更频繁、更隐蔽。看似我们有了更多选择,实则每个选择的变量更复杂、更多变。
不同的是,古人面对不确定,是把它纳入日常节律之中,比如节气、祭祀、耕种轮替,想从种种变化中找出 「不变」 之机。科学主义带来一种迷信,让受过教育的现代人总想掌控变化、对抗变化,于是有了无休止的日程表、KPI、人生的长短期计划。越想掌控,失控感反倒越强。
卡尔维诺在 《看不见的城市》 里说,「未来不是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片需要我们穿行的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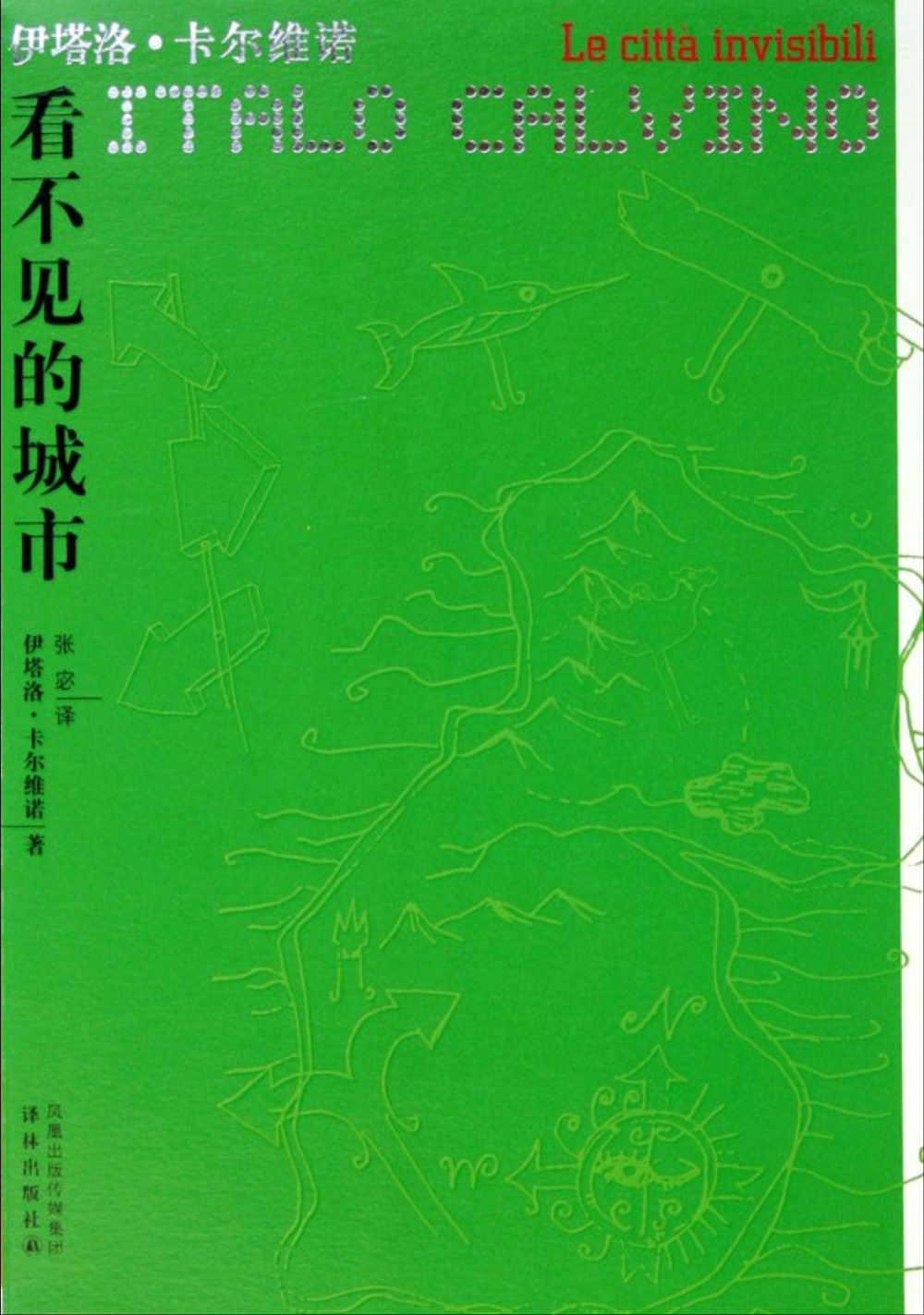
他把 「走到哪里是哪里」 从一个看似消极的口头禅,变成了一种探索姿态。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漂泊,那就是行走在一张无法完全绘制的地图上,边走边发现、边发现边调整。
在一个不能完全靠想象去了解的国家,我每次为长途旅行做攻略,根本无法奢望能事无巨细详尽覆盖。途中遇到的高温、暴雨、住宿选择、临时展览、农夫集市……真正的乐趣往往是这些 「意外」 带来的,没错,计划就是用来打破的。
当变化突然而至,有人会出于习惯抱怨、后悔或恐惧,我会深呼吸一会儿,看到这种恐惧与不确定带来的不安,然后用一种 「兴奋的平静」 来迎接它。
我在树林弯道里、在我的书桌前反复确认过:未来不必压垮今天,过去也不用拖累今天,只管走好眼前这一步。下一步,自会显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