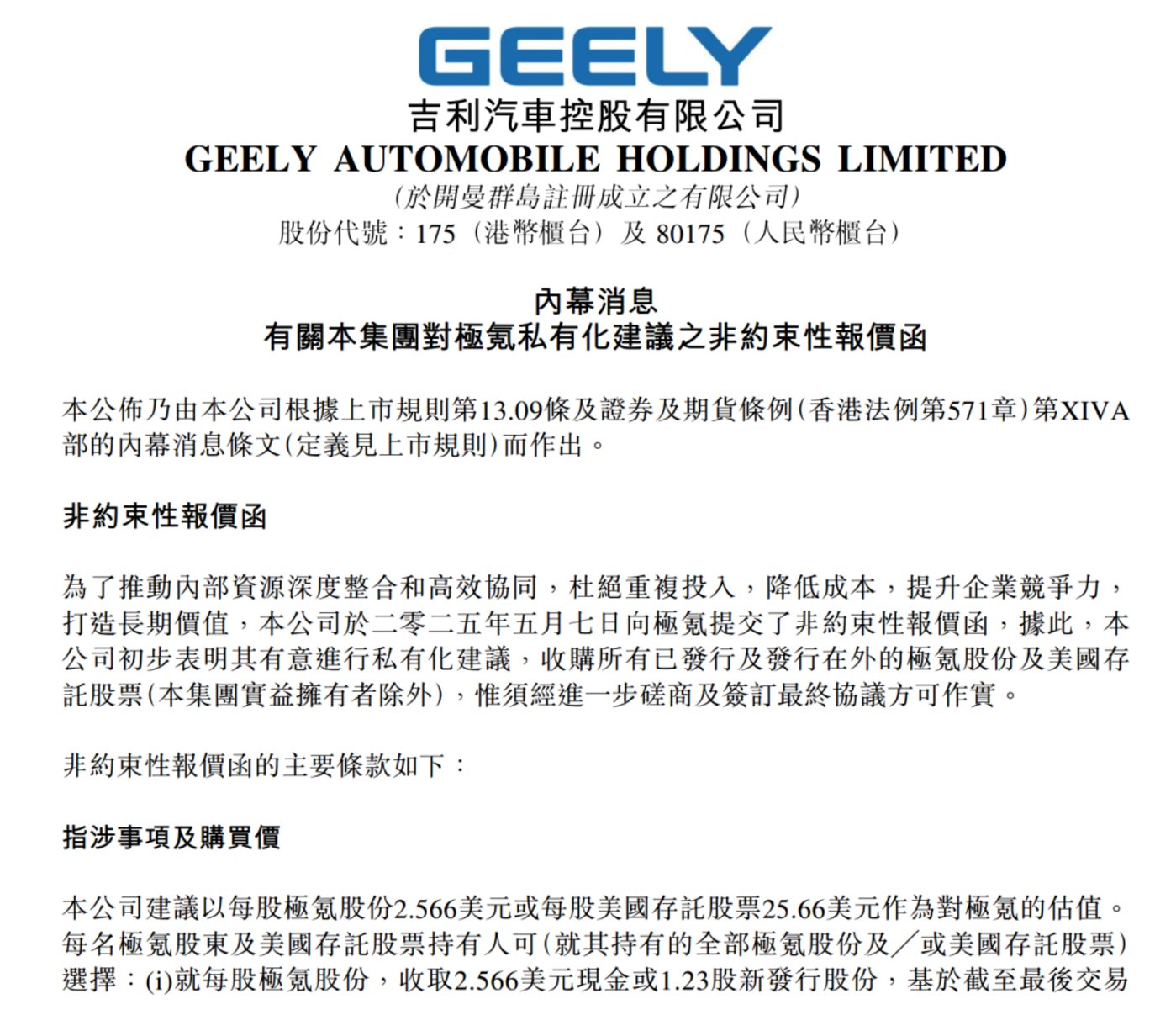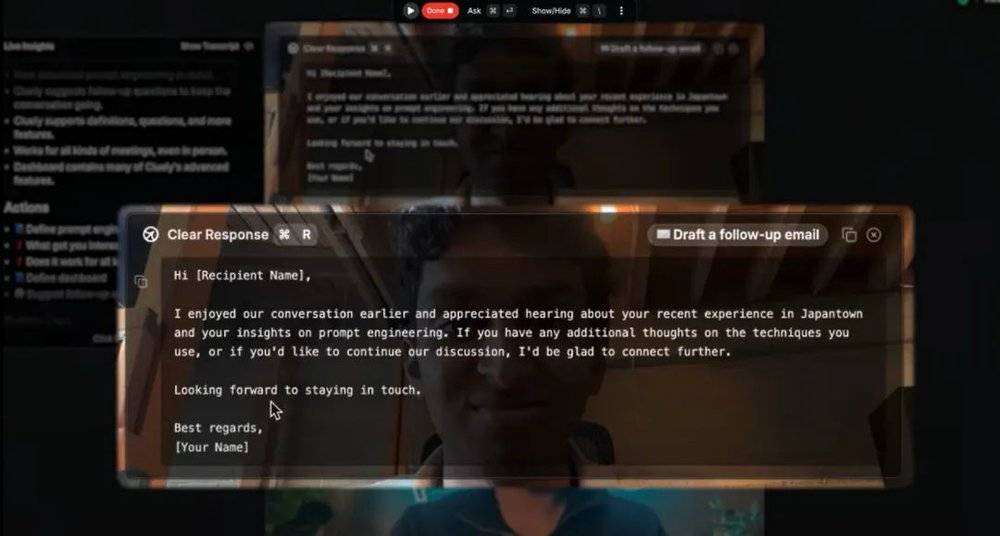菠萝:意识这个东西是人特有的吗?还是别的动物也有?
宇晨博士:如果你家里有小猫小狗,一定会觉得它们也是有自主意识的。例如有时候小猫可能会故意报复你;你带小狗出去玩,它不想回家,就趴在地上撒娇……
所以我觉得它们一定是有意识的,只不过它的意识存在方式可能跟人类不太一样。甚至不光是猫、狗,一些低级动物 (例如蚂蚁等)都有可能是有意识的,只不过它们的意识存在方式比较独特,是我们人类还不能理解的一种存在方式。
菠萝:很多人认为蚂蚁没有什么特别的自我意识,它们是随着生化的信号,每个个体做一些贡献,最后形成一个很庞大的蚁群,产生了一些生物学功能。但你认为个体的蚂蚁也有意识?
宇晨博士:准确来说,我们是无从可知的,从严苛的科学角度来说,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旁边的这个人是不是有意识。因为意识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东西, 「我是怎样去体会世界的?」「我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没有 「魂穿」 他、没有到他的大脑里,其实完全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只能通过推理得出结论。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法证明任何一个另外的个体是对世界有体验的、是有意识的。
菠萝:刚才讲到,要有 「我」 的这种体验,那这个意识和平时说的 「自我意识」 是一回事儿吗?就得有自我才有意识吗?
宇晨博士:我觉得是一回事儿。自我意识里,「自我」 这两个字是最关键的,也就是我置身于世界,我是怎么样去体会这个世界的,无关乎别人。
菠萝:如果不是自我意识,那就完全是机械地响应外界信号,然后做出反应。
宇晨博士:对。
菠萝:所以科学家有没有定义什么是意识?
宇晨博士:其实我们做科学研究,通常要先祛魅。先不要觉得意识是一个非常玄妙神奇,或者非常形而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还原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层面。意识就是经验和体验——我们怎么样去体验世界,体验周围的一切,以及我们通过这些体验怎样做出自我选择、怎样去认识自我。
菠萝:意识肯定是在脑袋里的,那它藏在什么地方呢?
宇晨博士:不同的理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人认为意识存在于前额叶,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大脑的后部,有些人认为是很小的一个区域,叫做屏状体,它和大脑各个区域的连接都非常紧密。还有人认为意识存在于丘脑,这也是认知信息、感知信息的一个闸门。
意识这个东西,很难存在于一个非常狭隘的解剖结构里,因为它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大家经常说意识不是一个孤岛,它是信息的流动。比如说我去体验一件事情,我要感知它、处理它、认知它、决策它,最终形成一种体验。所以这么一系列复杂的功能整合,很难由很小的一个脑区去单独执行。所以整个大脑在意识层面中都起到一些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这个重要性可能有高有低。
菠萝:开车的人经常会有这种感觉: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开车的事儿,但还是顺利到了目的地,也不闯红绿灯、也注意了行车安全。这算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呢?
宇晨博士:这可以算是无意识。可能大家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谈话,旁边其实放着一个显微镜,但在我说之前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它是在这儿的,也就是说没有处在意识层面。
这里又要说到另一个概念,就是 「注意力」。注意力和意识是紧密相连的。所有信息传输到大脑之后,大脑是要筛选这些信息的。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处在注意力的中央,那它就不会进入意识层面。但这些信息在不在大脑里面呢?其实是在的,只是没被注意到,没有进入到意识处理的层面。
菠萝:然后这些信息就没了吗?
宇晨博士:没错,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是曾经存在过的。
菠萝:我听过一个说法,如果人们接触的所有信息全部都留在脑子里面,人肯定就疯了。
宇晨博士: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系统,不能处理无限的信息。
菠萝:刚才我们提到驾驶汽车的状态,这还算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那如果是昏迷或者麻醉状态,以及睡着之后无意识的状态,这几种状态有区别吗?
宇晨博士:在科学上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是它的触发方式不一样。比如说睡眠,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无意识状态。每个人都需要睡觉,睡眠其实也有不同的阶段。深度无梦境睡眠是没有意识的,有梦境和浅度睡眠还是有一定的意识存在的。
如果大家做过大手术或者胃肠镜,经历过全身麻醉,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接受麻醉之后会觉得自己的这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其实时间并没有消失,只是你对这段时间的意识和记忆消失了。而麻醉的药物机制就是抑制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性。
同时还有其他的机制,比如说脑创伤导致的昏迷或者植物人,可能是外力作用导致了一些脑部损伤,使其不存在意识。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机制、方法触发人进入没有意识的状态。
菠萝:从神经的反应来看,如果去测试睡着的人和植物人,能从什么信号里面看出来他是处于有意识、还是没意识的状态?
宇晨博士:从脑电图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来,昏迷的病人、植物人、深度睡眠的人,他们在脑电信号上是有一定共性的,这个还是比较清楚的。当然也有差别。比如说我们睡眠时有一个很经典的脑电信号叫做纺锤波,如果做睡眠分析就一定要看这个特征。睡眠和麻醉时有共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它们各自的纺锤波一个叫睡眠纺锤波,一个叫麻醉纺锤波。
菠萝:说起植物人,有没有可能这个人看起来是昏迷的,但也许他是有意识的,只是他说不了话?
宇晨博士: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临床上有一些这样的病人,他可能不是处在完全的植物状态,而是处于 MCS,一种微意识状态,就是说有微弱的意识,但是不能对外界的声音或者触碰做出反应,这种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好评估的。
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实验范式,例如运动想象范式,配合功能核磁就可以分辨。我们会告诉病人,请想象你在打篮球、请想象你在喝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观测到他的运动皮层有一定的响应。尽管他在表面上好像没有意识,但其实大脑里还是有一些微弱的意识状态。对于这些病人,临床上可能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电刺激或一些其他的方式,争取让他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水平,尽管这比较困难。
菠萝:所以听觉可能更顽固一点,更稳定一点。有可能听觉还保持,但是行动能力没有了。
宇晨博士:是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从方法角度来说,听觉是比较好监测的,但对于有些病人,如果想要做视觉测试是困难的,例如很多昏迷的病人是闭着眼睛的,我们没办法拿一个牙签给他眼睛撑开,然后再给他做测试。
菠萝:大家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当自己到了生命的终末期,在 ICU 里,其实自己有意识,但是动不了,还被插了很多管,想想就非常痛苦。但是根据你的说法,这个人有没有意识,其实是可以监测的对吧?
宇晨博士:现在临床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先进一些。有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些临床医生的会议,就觉得很多医学技术的先进程度让人非常震惊。就比如刚才说的监测昏迷病人或者植物人是否有一些微弱的意识存在,做得就比较前沿,并且效果非常好。不光可以从大脑神经信号的角度来诊断,还有各个科室 (包括康复科、急诊等)各种方法的配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担心。现在临床做得非常规范,也非常先进。
菠萝:潜意识又是什么东西呢?
宇晨博士:潜意识的科学定义比较模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就像你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骑自行车,这个其实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潜意识。
菠萝:那平时我们说的直觉,比如我遇到一件事,就觉得应该如何干,但好像脑袋并没有做决策这个过程,这也算潜意识吗?
宇晨博士:我觉得这可以算一个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过程。人体有好几种无意识的状态,比如无意识视觉,就是我视野里有这个东西,但我没有注意到它;或者无意识听觉,比如我们俩出去吃饭聊得热火朝天,可能旁边那一桌也在说话,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直觉属于一种无意识的决策;这种决策是非常快速的,可能是基于我过往的一些人生经验。比如有些消防员到一个地方救火,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决定:这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尽管他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和逻辑推理去证明这个事情,但是他有直觉,可能就是基于他的以往经验。因为他重复做了太多次,形成一种固定的大脑环路,所以再做决策就不需要思考,直接到达决策终点,可以算是一种无意识的决策过程。
菠萝:意识这个东西怎么去研究?要借助一些工具吗?
宇晨博士:研究意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正常清醒的状态下去研究,它的一个目的就是剥离对世界的初级感知和更高层面的意识。比如说我可以让这个人去看一个东西,然后逐渐把这个图片的对比度降低,慢慢他就觉得我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这个信息依然是进入到初级视觉皮层的,所以这个信息是在大脑里面的,只不过没有进入意识层面。
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操作的方式去创造这种剥离,这是在清醒的健康人中可以做到的。另外在健康人身上,在麻醉、深度睡眠这两种状态下也是可以去探究意识的。
我觉得在动物上研究意识可能比较牵强,因为我们研究意识的核心是想要知道人的存在本质是什么?什么叫人的自我意识?为什么我是我、你是你?
动物虽然有意识,但是它和人的意识差太多了。我们平时用小老鼠,也知道它是有意识的,它有自己的社交活动、它要吃饭、它会觉得饿、它似乎可能有时候也有一些情感层面的存在。有时候研究抑郁症也会用到老鼠的模型,但它的意识跟人相去甚远。所以从模型的角度来说,研究意识还是用人最好。
除了在健康人身上研究,第二种研究方式就是在一些有意识障碍的病人身上探究,比如昏迷、植物人,还有微意识状态的人,都是可以去研究的。在这些人当中,他的意识状态是有问题的,或者有时候他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神经活动到底和正常清醒有意识的人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科学方法,就是对比没有意识和有意识的状态。
菠萝:大家眼中的 「疯子」,就是神经不太正常、天天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他们是有意识的吗?
宇晨博士:他们其实很有意识,只是思考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感知、有判断,也能基于信息做出决策。尽管决策在我们看来很疯狂,但是他们是有自己的意识的。
其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识,即使是正常人。例如你和小明出去看到一个风景,会觉得怎么就是跟这个人眼中所得美景不同、话也不投机?但和小红出去,可能就觉得真是相见恨晚。一个人在不同成长阶段中,或者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意识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们可能非常幼稚、天真、快乐,自我意识和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体验,和我们到了更大的年龄 (30 岁、40 岁、80 岁)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是在同一个个体当中,我们的意识状态的存在方式也是会有变化的。
菠萝:那在意识这个领域,或者你当时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哪几个研究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宇晨博士:当时我看到一个实验叫做双眼竞争,就是给两侧不同的视野展示不同的图片,也就是说左眼看到的和右眼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大脑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信息?
可能大家会觉得,应该看到的是两张图的融合,比如说左右分别是一个苹果和一个香蕉,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可能既像苹果又像香蕉,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同一时刻我们的大脑只能处理其中一个信息,偶尔我们会看到苹果,偶尔我们会看到香蕉,但看到苹果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看到香蕉,看到香蕉的时候就一定不会看到苹果,两个信息是动态交替的传入到大脑当中的,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同时的传入到大脑中,是轮流进来的,这就叫做双眼竞争,它是一个竞争关系,不是一个合作关系。
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更加神奇的是:给一只眼睛去看一个静止的图,另一只眼睛去看闪烁的一些斑块,五彩斑斓的斑块。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看到静止的图,有时候看到闪烁的斑块呢?也不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闪烁的斑块,对于那张静止的图我们一点都看不到,或者我们认为完全没有看到,所以这个闪烁的斑块完全占据了视觉意识。
这件事从机制上可能很难解释,还没有人探究得很明白,但是这个现象有鲁棒性 (稳健性),不管是你来还是我来做,都会出现同样的现象。那张静止的图进入我们的视野中,进入视觉处理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更神奇的是,假设我们这张静止的图片是一个带有情绪的人脸,可以是一张悲伤的脸,可以是一个生气的脸,我们还是看不到,永远只看到闪烁的斑块。但是我们的杏仁核 (大脑当中的情绪处理中心),却能分辨出这个脸是一张高兴的脸还是悲伤的脸。所以这个信息不光进入到视觉层面了,还进入到情感处理中枢了,只不过最终它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
菠萝:怎么能知道杏仁核知道这个东西的呢?
宇晨博士:最初是用的功能核磁,它能够区分这两种状态的区别。
菠萝:所以你的大脑里其实已经产生反应了,但是都没有进入意识层面。这还有点让人绝望,我们经常呼吁大家要多看书,少看短视频,但按照这个实验来看,如果有短视频在那儿闪,我抱一本书也没有用,我的意识层还是想看动的那个短视频。
宇晨博士:把两只眼睛中间这个挡板拿掉就好了,在同一个视野里,一边短视频,另一边是书,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前额叶控制的中枢就能够起作用。这个时候我是要狠下心来完整读一本莎士比亚,还是看短视频,就需要前额叶去决策了。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这种延迟满足,喜欢学知识,就选择去读一本莎士比亚;可能有些人不太想做这个努力,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非常累了,就是需要休息,就选择看一看短视频也没什么关系。
菠萝:用动物模型研究意识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宇晨博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评估动物意识的实验,叫镜子测试。如果一种动物看到镜子,能知道镜子里的像是自己,那么它就是有非常高等的智慧和意识的,是有自我意识的。
菠萝:也就是说它能区分镜子里的是自己,而不是另外一个个体。那要怎么知道镜子里和自己是一样的呢?
宇晨博士: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没有父母或者亲朋好友教我们照镜子这件事情,人能不能在没有任何外界教育的情况下,知道镜子里是自己。我非常想做这样的实验,可能有些人也做过。大部分动物是没有办法从镜子当中去判断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反而有一种鱼类,有照镜子的能力,它可能知道这个镜子里面是自己。至于为什么,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很多衡量参数去论证它知道镜子里是自己。
菠萝:现在有测谎仪,可以看脑电波,有没有什么仪器能够更准确地看出一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事儿?
宇晨博士:可能会有一些方式。有些人做过用功能核磁去监测病人看电影的时候的脑活动,那么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把他看到的一些视觉特征给重建出来,这是能够做到的。尽管现在做得还比较粗糙,但我觉得已经非常神奇了。
测谎仪,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bug,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这个人不断地去说谎,说着说着他自己都认为是真的了,那如果他自己都认为是真的,我们又如何从客观的角度从他的大脑活动里得知这个是假的呢?这在他大脑里是一个真相,如果能测,那我们测到的东西就相应来说也是一个真相。所以我个人觉得用测谎还是不如客观的证据来得有效。
菠萝:很多人说,人死亡以后其实意识是会存留一段时间的,你相信这事儿吗?
宇晨博士:我觉得有可能会短暂存留。因为意识这个东西需要一个动态系统去支持,人脑就是一个动态系统,可能当人死后,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内,大脑的神经活动还有一定的活性,这个时候也许是会有意识状态存在的。但当这个人死透了,完全没有任何的活性了,神经元之类的也都死了,那他应该就没有意识了。
菠萝:死亡是有心跳这种判断标准的,在医学上还有脑死亡的状态,那脑死亡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意识了?
宇晨博士:对,我认为脑死亡是没有意识的。
菠萝:根据你们的研究,未来是否有可能通过一些方式来增强背东西、记忆的效率?
宇晨博士: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哆啦 A 梦动画片,里面有一个记忆面包,往书上摁一下、吃下去,这个东西就记住了,我就非常喜欢这种东西。我觉得以后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有些实验室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在人记东西的时候给他施加电刺激,那么这个电刺激可以增加或者减弱神经元的活动,发现是可以增强记忆的,不光有理论支持,还有实际观察的支持。
菠萝:感觉可以开发一个东西,人背书的时候嗷嗷地电,电完记得更牢 (当然不是那种电击,是比较微弱的电……)。最后我想聊聊比较前沿的一个东西,你怎么看待意识在未来的发展?现在人工智能研究非常活跃,你会担心人工智能突然产生意识吗?或者你觉得理论上是可能发生的吗?
宇晨博士: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发生的。意识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 Christof Koch,他认为人工智能是没有意识的。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观点,它们是有可能产生意识的。比如现在的 AI 大模型,我们在使用时,当你很礼貌地问它和当你命令式地去问它同一个问题,给你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已经能从我们的大语言数据当中去学到一些礼貌和不礼貌的蛛丝马迹。那没有道理学不会这里面存在的其他东西,不管是感情还是意识、还是更深刻的一些思考,都是有可能学会的。
而且我也比较担心,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工智能突然有了意识,或者有了一些自我的想法,有了感情,它生气了,那真的有可能对人类发起攻击。所以我认为管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最新的科技当然是好处很多,但我们也要去提前预见这些可能带来的风险,这需要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去提前预见,并且做好防范。
菠萝:确实很少有神经生物学家,或者学生命科学的人来讲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学计算机的人会有很多的担心,觉得 AI 会产生意识。那你觉得跟 AI 说话应该对它礼貌一点,还是凶一点?
宇晨博士:礼貌一点,有的时候结果会更详细一点。比如同一个问题,「请您帮我梳理近十年意识领域研究的文献」,然后另一种问法 「近十年意识领域文献」,第一种方式会给你梳理得更精细一点。
菠萝: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自己做一个预测,50 年后,你觉得在意识领域会发生什么事情?
宇晨博士:我觉得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学科。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说意识的研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今天可能连半步都没有走完。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我都不是很清楚在人类灭绝之前,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研究透彻。但我觉得没有关系。科学领域里面有两个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宇宙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物理学要做的事情。第二就是人的思维,人的意识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神经科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要做的事情。
这两个最深层的问题,最终能不能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不断挑战自己的智慧,不断拓宽知识的边界,哪怕八千里路我们就走了半步也没有关系,我们还在往前就好了。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说,你不要总想着这是一件很困难、难以完成的事情,科学探究可以是一场浪漫主义,如果说我们注定找不到那个终极的答案,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浪漫的科学探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菠萝因子,作者:80 后菠萝博士、肖宇晨,文字整理:佳韵、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