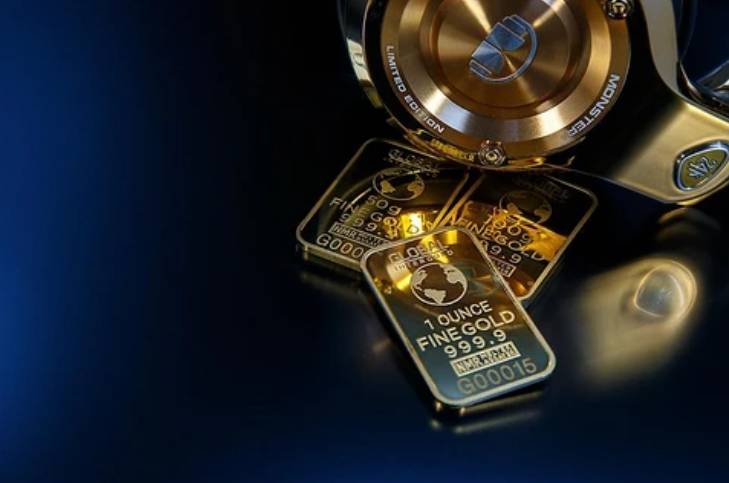文 | 光子星球
2004 年雅典奥运,刘翔以 12 秒 91 打破奥运纪录,把一枚田径金牌带回了一个此前并不以短跑著称的国家。
比赛结束不久,一支广告迅速上线:起跑、腾空、跨栏、冲线,被剪辑成凌厉的蒙太奇,配以设问:“ 亚洲人缺乏爆发力?缺乏必胜的气势?”—— 不等观众回答,刘翔已然冲线庆祝,“ 你能比你快” 的广告语随之浮现。
这支广告,属于耐克。
彼时的耐克,是少数能听懂中国,亦理解一个正在苏醒的国家,对“ 第一” 的渴望与自豪的品牌。
然而,二十年后,这种连接逐渐松动—— 从渠道体系,到产品叙事,再到品牌形象,耐克慢慢困在自己编织的网中,曾经滚烫的品牌叙事,变得遥远且模糊。
财报显示,最新财季,耐克大中华区营收同比下滑 21%,降至 14.8 亿美元,已连续多个季度走低。电商业务下滑 31%,批发渠道下滑 24%,自营门店亦下降 6%。这个曾经的“ 优等生”,成绩正迅速滑坡。
数字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裂痕,是那种渐渐消退的,品牌与时代之间的“ 共谋感”。
而当下的耐克,正在积极自救:艾略特· 希尔回归、Win Now 战略启动、产品更专业、渠道更包容、品牌精神亦试图回到原点。
一切都像是教科书式的应对,但问题似乎并不在“ 对” 与“ 错” 本身。
为了热钱,卖掉信仰
在中国市场的多数年份里,耐克几乎不需要主动奔跑。
彼时,尚处品牌力主导市场的时代,耐克几乎是一家“ 躺赢” 的品牌—— 连续二十个季度的双位数增长让“ 竞争” 这个词显得多余,没有敌手,只有臣服。
但任何长周期的繁荣,往往都藏着迟来的问题。赢得够久,难免会高估自身的自洽能力,即便出现裂缝,也容易被解释为“ 纹理”,直到市场哗然收水,惯性失效,问题才一并涌现。
炒鞋,是最早传出的异响。
2019 年前后,球鞋市场骤然升温,迅速被二级市场资本化。
社区的语言也随之更换,球感、脚感逐渐被边缘,取而代之的是涨幅、货量、编号、补货节奏—— 一双鞋被当作股票,反复拆解、追踪、博弈。
品牌制造稀缺,转售缔造溢价,两者形成闭环。短期来看,此番打法相当奏效,诸多潮流品牌、潮玩玩家,都曾照此运作。
对品牌而言,它更适合制造声浪,难以承载增长。鞋市也好,潮玩也罢,本质上一种脆弱的繁荣—— 不创造价值,只加速透支品牌的未来预期。也因此,真正清醒的玩家,往往在热度见顶前抽身,及时收回对市场的控制权。
偏偏那时的耐克,正好把方向盘交给了一个只顾着踩油门的人。
2020 年,约翰· 多纳霍出任耐克 CEO。
彼时,AI 尚在酝酿,数字化转型仍是企业叙事的主线。此番语境下,咨询行业出身的多纳霍非但没有祛魅,反而自带光环。
作为职业经理人,其承担着“ 用先进方法论改造传统品牌” 的期望与压力。而球鞋市场的爆发,恰好是难得的机会—— 可被整合、可被放大,更重要的是,可以立刻做出成绩。
而 DTC(Direct to Consumer) 模式,自然成为了最清晰、也最稳妥的路径。
全球语境下,DTC 被视为顺理成章的效率改革:Nike App、自营门店、SNKRS 社区…… 一整套新零售阵列迅速铺开,几乎满足了组织内部对“ 数字化成果” 的全部期待。
对外,它讲的是“ 更贴近消费者”;对内,则更像是对“ 中间商赚差价” 的清算—— 剥离代理、压缩空间,把流量和利润统一纳入品牌自己的闭环里。
与此同时,DTC 改革让耐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权。
传统分销体系下,货品一出库,品牌便随之退场,在自有渠道中,耐克则能掌控节奏与流向;而用户的每一次浏览、预约、抽签、支付数据,亦将被收录、分析—— 一款鞋是否能火,不再依赖终端滞后的售罄或排队来验证,而是由系统前置感知。
基于此,鞋市狂热中,耐克虽未亲自下场,却始终在场,并在幕后主导了筹码的分配:限量制造稀缺,情绪升温后择机补货,节奏总比市场慢半步,却永远踩在利润点上—— 不留口实,也从不空手而归。
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2 年,DTC 的营收比重从 32% 提至 43%,SNKRS 与 Nike App 在部分区域市场甚至一度取代门店,成为发售主渠道。
一切似乎都在提效,改革也推进得异常顺利。殊不知,高歌猛进的表象下,正悄然酝酿着危机。
在 《鞋狗》 中,耐克创始人菲尔· 奈特曾给“ 鞋狗 (Shoe Dog)” 留下过近乎私人化的定义:那些全身心投入制鞋、卖鞋、买鞋或设计鞋的人。这个词听上去带点自嘲,却始终保留一丝敬意—— 只有真正爱过鞋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称呼。
约翰· 多纳霍显然不是“ 鞋狗”。
他对鞋没有执念,对“ 运动” 也没有执念。他的世界建立在指标之上,组织、渠道、业绩、KPI 才是他最熟悉的语言。
因此,自他上任起,耐克越来越像一家“ 公司”,而不像一个“ 品牌”—— 标准化与业绩优先的逻辑,像网一样收拢着这家企业曾经的野性与多样性。
最典型的,是组织重构。
约翰· 多纳霍主导下,曾经围绕“ 篮球”“ 跑步”“ 训练” 等构建的架构,被“ 男/女/儿童” 的三大类别所取代。这看似更贴近用户结构,实则是品牌精神的消解:品牌不再以运动为内核展开叙事,而转向清晰、需求扁平的消费单元—— 耐克与运动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抽象、遥远。
这种“ 效率优先” 的逻辑,在中国市场的另一端,撕裂得更为剧烈。
无数存在于中国灰度地带的中小代理商,本就在此前品牌集中化的趋势中迷惘、淡出,DTC 改革提速后,尾部渠道几乎全线沉寂。而像滔搏这样的头部分销商,也开始感受到压力—— 热门款、限量款的配额愈发稀薄,渠道价差逐渐失去腾挪空间。
问题在于,无论是滔搏这样扎根低线城市的中间层,还是那些与体校、体委长期共生的老分销商,虽在“ 效率” 视角下被视作冗余,却是品牌触达社会肌理的“ 毛细血管”。而挥动着直销重拳的耐克,好似把品牌从更广域的消费土壤中拔了出来。
最终,泡沫在膨胀中破裂,耐克的精神肌理亦被掏空。以至于热潮退去后,品牌开始遭遇断层:一线城市的门店陷入库存与打折的恶性循环;下沉市场则因触点坍缩,逐渐失联。
盛世之下,品牌精神止于沉默。
灵魂的重量
很多时候,当一家企业步入动荡周期,权力的重构往往会先于战略选择浮出水面。
尤其当组织需要对抗阻力、推动争议决策—— 比如激进转型、变革渠道、削弱既有盟友体系时,往往不会由真正的“ 核心” 来出面,而是将任务交由“ 合适” 的人,比如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或将恰好处在边缘位置的高管推向台前。
后者看似站在聚光灯下,实则身处风暴中心,既是改革的执行者,也是后果的“ 背锅人”—— 以“ 个体” 之名,完成组织层面的泄压与兑责。
因此,不能将一切后果粗暴归因于某位 CEO 的判断,毕竟很多所谓的选择,是组织惯性下的必然。
以大中华区为例,炒鞋热退潮,并不等于需求坍塌,而是品牌回归正常的生长节奏。可此后几年,耐克却未能重拾增长,自然有着更深的原因。
据悉,耐克采用典型的矩阵式结构,全球主导产品与品牌,区域负责渠道与执行。大中华区虽设总部,却不免束于“ 中央集权”,难以展开独立的战略定调与叙事框架,甚至就连核心的鞋款设计,亦集中于俄勒冈。
扩张阶段,它是一种秩序;收缩阶段,则成了拖拽—— 越是追求一致,越容易压制局部的反应力。
《重新定义公司》 中,施密特指出,组织效率并不取决于结构多坚固,而在于反馈机制的灵敏。“Speed matters”—— 速度远比层级体量更关键。而耐克过去有完整、厚重的组织体系,却鲜有应对突发变化与局部异动的“ 敏感神经”。
这点,在某次国内舆论风暴中,暴露得尤为彻底。面对群情激愤的大众情绪,耐克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迟钝—— 回应滞后、表态迟缓、措辞僵化。
表面看,这是公关失控;深层看,则透着耐克全球架构的长期积弊—— 本意是为了控制复杂性,但最终却封闭了对复杂性的感受。
后果可谓相当严重,多年铺设的 KOL 体系哑火,明星代言相继切割,用户心智塌缩…… 一个全球品牌的感知力,在它最需要共情的时刻,彻底坍塌。
随着业绩连季承压,组织文化持续钝化,耐克终于意识到,问题不再是“ 鞋卖不动” 这么简单。
2024 年,它开始向内回望。
这一次,耐克没有再用“ 市场疲软” 做挡箭牌,也不再指望靠单点产品或营销奇袭挽回局面,而是直接对权力轴心动刀。
修复,从最顶层开始。
创始人菲尔· 奈特重新现身,召回老将艾略特· 希尔,并提出 Win Now 战略—— 这位从门店销售一路爬升至全球品牌总裁的“ 鞋狗”,被寄望于唤回那个旧日耐克的精神质地。
相比偏好指标与 Excel 的多纳霍,希尔显然更擅长处理那些无法量化的部分—— 品牌气质、文化肌理、组织叙事等层面的“ 软组织撕裂”。
比如在品牌张力迅速消退的国内市场,耐克启动了本地创意中心 Icon Studios,放权本地内容团队,尝试打破过去“ 全球叙事、区域执行” 的旧秩序。
几乎在同一时间,耐克中国区也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人事更替:外籍高管退场,由来自中国本土、在耐克体系中成长二十年的董炜担任大中华区董事长兼 CEO。
这一系列操作,似乎释放着某种信号—— 一贯强势的耐克,似乎在区域治理上释放出更大的弹性。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结构性松动已然发生,但至少表明,耐克正在重新理解“ 本地适应性” 的组织逻辑。
更深层的变化,也潜藏其中。
从倚重“ 通才”,到相信从内部爬升、亲历品牌每一寸演化的“ 内生者”,耐克似乎终于明白—— 想要救品牌于水深火热,需要懂它、爱它、扎根于它的人。
往回走,也往前去
人与组织的问题,归于内部,尚可凭组织意志纠偏;外部挑战则客观存在,不因组织意志而转移。脱离泥沼,再植土壤,才是更漫长、更现实的部分。
整体来看,Win Now 战略像是一种回拢:重拾运动文化叙事、修补渠道关系,对过往的激进打法进行拨乱反正。
其中很多动作,本质上是“ 还债”。
比如产品线的收放。以 Dunk 为例,2019 到 2022 年间,其推出了两百多个配色,几乎月月上新,沦为“ 调色盘”。而大水漫灌之下,Dunk 原本的街头、反叛气质被透支、消解,最终淹没在库存之中。
突然走红的演员,往往需要在热度顶峰及时抽身,才能避免被角色定义一生。而耐克现阶段正将其三大经典鞋款 (Air Jordan 1、Air Force 1、Dunk 系列)“ 从主角位撤出”,以修复产品叙事的密度与梯度。
与此同时,耐克开始回头,重返那个曾最擅长的场域:专业—— 技术鞋款回归中心,也更愿意将预算砸向技术。
对运动品牌而言,追求专业自然是对第一性原理的回归。但也正因如此,“ 专业” 本身,很难成为“ 选择”—— 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块基石上,分野,注定只能来自别处。
事实上,过去几年间,国内用户偏好正悄然转移—— 从追求胜负、速度、极限,转向了呼吸、松弛与生活方式。而讲了几十年“ 赢” 的耐克,却几乎缺席了这场近些年最温和、也最彻底的运动消费迁徙。
其实,耐克并不是没有户外基因。1989 年,其就曾推出名为 ACG(All Conditions Gear) 的专业产品线。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里,ACG 几经沉浮,反复被提起,又反复被遗忘,从未真正扎下根来。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前后,耐克曾请来潮流“ 黑武士”Errolson Hugh,为 ACG 改头换面。他用极简、先锋、机能等语言,为这一老牌支线注入了时尚血液。而被改造后的 ACG,一度击中了“ 潮流圈” 的审美,但也逐渐丢掉了“ 为户外而生” 的初心。
最终,耐克留在城市,消费者却已经上了山。而安踏,则悄悄登上了神坛。
而现在,四处寻路的耐克,也终于开始“ 朝花夕拾”。ACG 全球 CEO 的职位,亦伴随着前述组织架构调整,一并交到了董炜手中。
将一个全球子品牌的控制权,交给一位区域市场负责人,背后自然有着更深的意味—— 此刻的耐克,或许并不那么需要户外,但却真的不能再失去中国。
归根结底,从人到组织,再到打法,耐克做着品牌该做的一切。只是,有些连接尚可失而复得,有些叙事则永远定格在当年冲线的那一帧画面中。好在,耐克重新回到了路上。
这一程,或许不是为了追赶谁,而是为了找回那个尚未走远的自己。
慢慢地,往回走,也往前去。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 (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 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