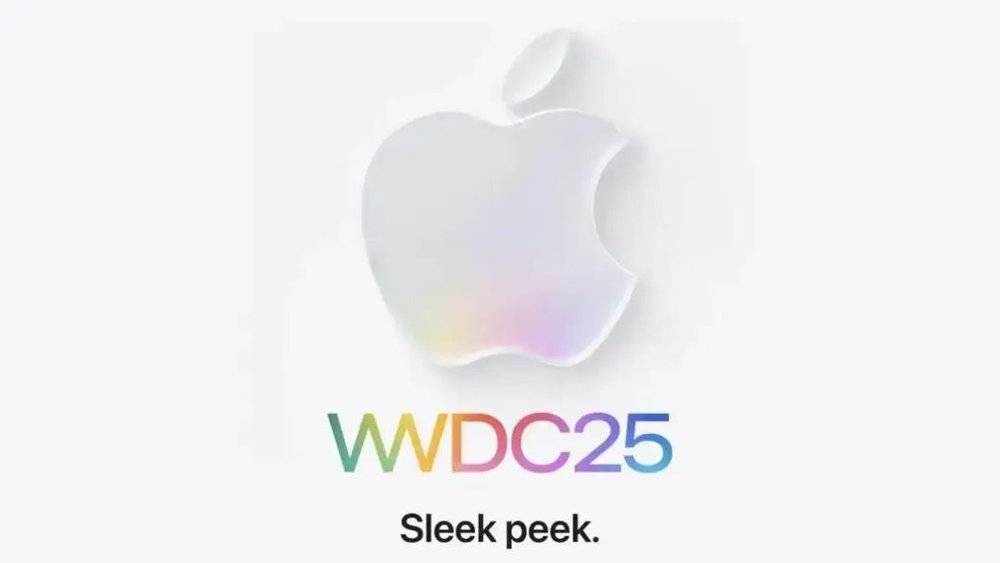文 | 空间秘探,作者 | 武爽
近期,长沙最大的民国建筑—— 国货陈列馆旧址,传出部分将改造为博物馆酒店的消息。它既不是单纯的博物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酒店,而是一种“ 混血产物”。这不是孤例。近几年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不断发生:天津、北京、广州、潮州、海口…… 一批“ 博物馆酒店” 正从小众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年轻人和城市文化的新入口。
长沙老楼“ 长出” 博物馆酒店
长沙中山路的一栋民国老楼最近引起关注。这栋建于 1932 年的“ 国货陈列馆”,外立面保留 16 根罗马柱,三层主体楼加中央四层塔楼,兼具民国工业风和欧式建筑风格。最新官方公示显示,这栋楼将进行保护性改造,其中部分空间将改造成“ 博物馆酒店”:不改变外观与主体结构,按历史建筑保护要求实施,同时腾挪出酒店功能面积,并拟设室外庭院与首层商业连通。
这幢建筑始建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是湖南最现代的商业展陈中心。建成之初,国货陈列馆承载着“ 国货当自强” 的使命,专营国货精品,广受市民欢迎。1938 年冬的“ 文夕大火” 中,国货陈列馆前栋亦被大火焚烧,但它四壁高耸,安然无恙。1949 年后,国货陈列馆改名为“ 中山路百货大楼”,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都是长沙最大的商业大楼,长沙人的时尚打卡地标。如今再被唤醒,它却要以“ 博物馆酒店” 的身份重新亮相。
据相关消息,国货陈列馆将被打造成 COJOY 共悦® 丨中山 1932,该项目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商业街区,包含潮流女装,咖啡,餐饮,烘焙,酒吧等综合性业态。1 楼主要为商业,2 楼为医美,3 至 6 楼为酒店,“ 目前正朝着 10 月 1 日开业的进度赶”。
和传统的文物保护不同,这次改造不是“ 封存”,而是“ 激活”。博物馆的展陈功能,将与酒店的住宿体验融合:客房区与展厅交错,旅客既是住客,也是参观者。有人说,这是长沙版的“ 夜宿博物馆”,但它远比电影中那个场景更日常、更可持续。
也有人问为什么不是“ 大商场续命”? 商业体量再扩张,反而会稀释这栋楼的叙事浓度。历史建筑的价值,往往不在“ 面积”,而在“ 故事”。把它做成“ 城市记忆展厅+可住宿的空间”,这是一个兼顾保护、活化与日常运营的折中方案:楼体不“ 硬改”,故事能“ 续命”,经营可“ 造血”。这恰好对应近几年国内多个城市的做法——“ 以酒店养博物馆”,或“ 博物馆里开酒店”,让公共文化空间摆脱“ 白天热、晚上冷” 的尴尬,连上真正的生活动线。
有网友称,如果把入住流程重新命名,Check-in 叫“ 检票”,大堂吧叫“ 导览厅”,客房是“ 沉浸展区”,走廊是“ 年代长廊”,退房是“ 二刷提醒”。会发现,酒店的每一个触点,都能成为展览叙事的一环。
谁在中国悄悄“ 玩” 起了博物馆酒店
什么是“ 博物馆酒店”?
简单来说,它是将博物馆功能与酒店功能叠加在同一个空间内,展品、展厅不再只是白天的参观对象,而成为住宿体验的一部分。住客不只是“ 游客”,更是“ 沉浸式的历史参与者”。
与“ 主题酒店” 不同,博物馆酒店强调真实的历史与文物,而不是简单的装饰与氛围营造。它的核心在于—— 让酒店空间本身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如果说长沙民国建筑改造为博物馆酒店的新闻只是一个“ 小火苗”,那么放眼全国,其实已经有不少“ 博物馆酒店” 悄然成势。它们并不属于同一种模式,有的强调历史见证,有的侧重艺术策展,有的甚至用“ 行业叙事” 来建构新的文化空间。不同的路径,勾勒出“ 博物馆酒店” 的群像图。
/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
楼下看史,楼上住史
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始建于 1863 年,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涉外饭店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 年,饭店内“ 天津利顺德博物馆” 正式落成开放。这是中国唯一一家在酒店内部设立、拥有国家文物局认证的博物馆。

利顺德博物馆面积近千平方米,展陈数千件珍贵文物,包括当年孙中山、胡适、张学良等政要下榻时的遗迹,以及天津开埠以来的城市变迁史等。利顺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酒店的“ 附属品”,而是有完整的票务体系、开放时段和独立的文化运营逻辑。游客可以单独购票参观,即便不在此住宿,也能通过博物馆了解天津的近代历史。
这种模式的亮点在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了“ 双轨并行”:一方面,博物馆本身增加了酒店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地位;另一方面,它吸引了额外的流量和收入来源,让“ 百年老饭店” 在商业上保持活力。对利顺德来说,酒店与博物馆的关系,不是点缀,而是互为支撑。
/ 上海和平饭店
袖珍馆,放大传奇记忆
如果说利顺德是“ 大体量博物馆” 的代表,那么上海和平饭店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 小而精”。作为外滩地标、Art Deco 建筑的经典之作,和平饭店本身已经是一个“ 活的博物馆”。但酒店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夹层开设了“ 和平博物馆”。
和平博物馆面积不大,堪称袖珍,但它的叙事密度极高。展览通过老照片、手稿、档案,浓缩了这座酒店从 1929 年开业至今的百年传奇。爵士乐、名流聚会、战时故事,这些片段被有机串联,构成了一部微缩版的“ 上海近代史”。
这种做法的逻辑是:用小体量的常设展,持续放大品牌记忆。对于住客来说,入住和平饭店,不仅仅是体验奢华的客房和黄浦江夜景,更重要的是“ 看见传奇的证据”。这种“ 记忆的物证化”,让和平饭店在全球豪华酒店的竞争中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标签。
/ 广州花园酒店
行业博物馆的自述
广州花园酒店整体是由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也是贝先生在中国留下的作品中,唯二两座酒店之一。(另一座是北京香山饭店) 它并没有仅仅展示本酒店的历史,而是在四层打造了约 1600 平方米的“ 酒店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由六个常设展厅、一个临展空间和一个多功能厅组成,主题并非地方文化,而是“ 酒店行业发展史”。展览内容涵盖了中国酒店业的兴起与演进,从 20 世纪的国营宾馆到当下的国际化集团,观众可以通过实物、影像和多媒体,理解整个行业的脉络。花园酒店博物馆也是国内首个以住宿业为主题的博物馆。
/ 北京奥加美术馆酒店
24 小时不打烊的展览
北京的奥加美术馆酒店,作为国内唯一拥有自营博物馆、美术馆的酒店,与其说它是酒店,不如说它是一个 24 小时不打烊的艺术展馆。在这里,每一层楼都是当代艺术展区,客房的布置本身就是展览的延伸。走进大堂、乘上电梯、进入房间,住客的每一步都在与艺术作品发生互动。对客人而言,住宿的过程就是一次完整的沉浸式展览体验。
这种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重构了“ 住客与观众” 的身份关系。住客天然成为观众,而观众如果选择入住,则进一步融入作品之中。
以上几个案例更多着眼于“ 历史” 和“ 艺术”,还有一些酒店的探索则强调“ 地方故事” 的沉浸感。
如寰海阁骑楼博物馆酒店,直接把骑楼建筑本身作为展品。骑楼的拱廊、立面和街区氛围,既是住宿空间,也是历史叙事的媒介。住客不需要去额外的博物馆,酒店本身就是一段海南开埠史。潮州“ 御酒店· 文凡臻选” 则结合了非遗与戏剧,打造“ 行进式剧场+酒店”。在这里,住客不仅住进了岭南古城的院落,还会在用餐、休憩过程中,偶遇地方戏曲、木偶剧甚至非遗手工展示。这种模式把“ 酒店” 变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微缩剧场,沉浸感极强。
这类案例的价值在于,它们让“ 在地文化” 不仅停留在展示层面,而是融入了住客的生活体验。换句话说,住客不仅是旁观者,而是地方文化的临时参与者。
文化赋能如何避免概念泡沫
在“ 博物馆酒店” 逐渐成为一个行业热词之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 文化+住宿” 的尝试。然而,真正能被称作“ 博物馆酒店” 的,并不是简单地在酒店大堂摆上几幅画、在走廊挂几张老照片,而是需要清晰的概念、严格的标准与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从天津、上海、广州到北京、海口、潮州,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做法:有的做大体量独立博物馆,有的开设袖珍馆,有的讲行业史,有的主打当代艺术,有的强调地方沉浸感。但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一是展陈不是装饰,而是灵魂。要让“ 博物馆酒店” 成立,而不是停留在概念炒作层面。在许多“ 伪博物馆酒店” 案例里,展陈往往被简化成装饰:挂几幅画、摆几个雕塑,更多像是“ 软装” 的一部分。但真正能成立的“ 博物馆酒店”,展陈必须成为核心价值,而非锦上添花。展陈需要有系统的策展逻辑和文化主题,与酒店的空间布局、品牌理念乃至所在城市的历史文脉相呼应。这种深度策展的力量,才能让“ 博物馆酒店” 从营销概念真正成为文化地标。
二是住宿不是功能,而是入口。传统的博物馆参观往往是“ 一次性” 的,观展结束即离开,文化体验难以延续。而酒店的独特价值在于,住宿过程天然是一个沉浸式、长时间的“ 停留”。这一停留过程,如果嵌入了文化叙事,便让住客不知不觉间完成了“ 深度参与”。如日本直岛的 Benesse House,既是酒店也是美术馆,住客白天看展,晚上还能在作品间自由游走,彻底模糊了“ 参观者” 和“ 住客” 的界限。
三是酒店正在成为夜间文化的容器。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多数在傍晚五六点闭馆,城市的文化动能在夜幕降临后戛然而止。而酒店本身 24 小时不间断开放的属性,使其天然具备承载夜间文化的潜力。近年来,从上海和平饭店的爵士乐演出,到成都东郊记忆的工业遗址改造酒店,再到北京的“ 艺术家驻留+酒店” 实验,都说明一个趋势:夜间文化正在从单一的餐饮、演艺,扩展到带有展陈属性的沉浸式体验。住客在深夜仍可随时进入展区观展、参加讲座或互动活动,而城市居民也能在下班后以轻松的方式走进这些空间,完成“ 下班— 观展— 夜宿” 的完整链路。酒店的夜间开放机制,恰好弥补了博物馆在时段上的空白,使文化消费真正进入“ 全天候” 时代。
城市更新因此有了新的方法论。过去的城市更新往往是“ 大拆大建”,以效率为导向,但这在存量时代显得粗糙,甚至破坏了城市肌理。相比之下,“ 博物馆酒店” 模式是一种“ 微更新”:保留建筑的历史形态与记忆,同时通过引入住宿与展陈功能,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例如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原本是近代租界的标志性建筑,如今通过常设展览和客房体验的结合,不仅留住了文化符号,也形成了稳定的运营逻辑。
博物馆酒店的未来畅想
“ 博物馆酒店” 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噱头,而是多方需求推动的结果。
从消费端来看,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对“ 住进故事” 的需求日益强烈。博物馆酒店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只是“ 展览+住宿” 的组合,而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转向。
在快节奏的城市中,人们越来越渴望停留时能获得意义感与身份认同。博物馆酒店提供的不是一间客房,而是一种“ 住进故事” 的体验:住客不只是过客,而成为城市记忆的临时参与者。无论是在走廊偶遇一张旧影,还是在庭院里邂逅一场非遗表演,那一刻,人们感受到的并不是“ 住过一间酒店”,而是“ 我曾属于这里” 的文化归属。
事实上,博物馆酒店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在于“ 展览+住宿” 的形式叠加,而在于它释放出一种新的空间价值逻辑。
对博物馆而言,引入酒店是一次“ 激活”。利用酒店 24 小时的开放属性,让文化场所不再依赖有限的票房和财政拨款,而通过住宿、餐饮、夜间消费形成滚动循环。而对酒店来说,博物馆功能的嵌入,则是一种“ 溢价”。在供给趋同的市场里,差异化是最稀缺的资源。与其在装修与设施上无休止内卷,不如通过“ 文化叙事” 塑造独特标签。一个自带文化历史的酒店,往往更容易获得关注,其空间价值已经超越了住宿本身。
不过,需要看清的是,这一模式并不具备普适性。并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建成博物馆,也不是所有博物馆空间都适合嵌入酒店。真正具备条件的往往是少数:有历史故事的老楼宇、有政策意愿的地方政府、有文化叙事价值的城市样本。换句话说,博物馆酒店更多是“ 稀缺资源的二次开发”,而非普遍可复制的行业模板。
也因此,我们看到的实践大多带有强烈的政府推动色彩。无论是历史建筑保护、夜间经济战略,还是城市文化品牌工程,博物馆酒店往往承载着公共政策的意图。市场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更像是“ 放大器”—— 把城市的文化意图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博物馆酒店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成为规模化赛道,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板:公共文化与商业逻辑并行不悖,甚至可以互为赋能。它历史文化重新“ 活起来”,也让酒店跳脱出价格战的泥潭。这或许也正是它最值得关注的商业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存量时代,城市空间的价值不在于数量扩张,而在于能否通过创新组合,实现文化魅力与商业活力的共振。
空间秘探认为,博物馆酒店不仅是一种空间创新,是一种文化与生活的融合实践。它让城市的历史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被感知,也让住宿不再只是功能性需求,而成为体验与记忆的承载。在未来,这种“ 文化+生活” 的融合模式或许会成为城市更新的新思路,让历史、艺术与商业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微妙而持久的共鸣。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 (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 App